


400-123-4567
13988999988


公司地址: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88号
联系方式:400-123-4567
公司传真:+86-123-4567
手机:1398899998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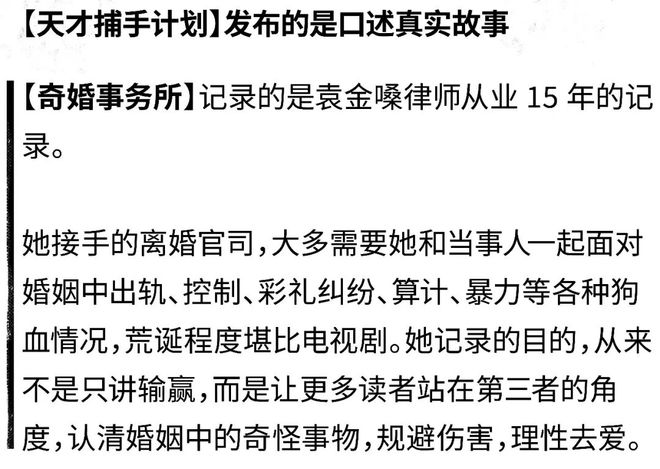 大家好,我是陈卓。最精彩的案件不是刑事案件,而是婚姻案件。 “这不是我说的,”我刚认识的一位新律师说。他的名字叫袁劲松。他说,在法律界,有人求财,有人求名。他不仅喜欢这些东西,还喜欢“自找麻烦”。他热衷于处理他能接手的最奇怪的离婚案件。我问怎么奇怪,他说反正比国产电视剧更荒唐。 “上帝是最好的编剧,但当他写关于人类婚姻的章节时,他一定是喝醉了。” 2011年,当他刚入行时,他心里就意识到了这一点,因为他接手的第一起离婚案涉及三个人的生命——两个人被谋杀,一个被判处死刑。这是她的婚姻案件第一次超出了普通人对离婚纠纷的想象。在这种情况下,客户发给他的消息是这样开头的——“法律叶媛,救救我。” “他又来了……” “他在敲门。我好害怕……”后来,他接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件,涉及欺骗、控制、彩礼、算计、暴力。它们伪装成家居用品,但往往变成了奇观。委托人害怕这些困难,也害怕面对离婚后的生活。在处理这些奇怪的人、奇怪的事时,他经常准备自己的金嗓子含片,因为无论是保护委托人,还是与对方律师争论,他的声音必须是美丽的。现在,袁劲桑决定把这个系列的故事叫做《奇怪的婚姻中介》,他想要记录的不仅仅是输赢,而是让更多的人站在第三者的角度,看清婚姻中的奇葩,避免伤害,理性地去爱,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,我几乎不会记得第一次见到小雅的情景。2017年深秋,我刚刚结束庭审,第一次见到了小雅。和大多数金融白领一样,她化着精致的妆容,穿着考究的衣服,坐着时背部挺直。他看起来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,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“袁律师,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的事情。”一如既往,我询问了主要情况:小雅,28岁,名校毕业,在当地一家金融机构担任业务骨干;她的丈夫陈文翰与她同岁,也是名校毕业,是她的初恋情人。他们结婚才一年多。婚前,陈文翰在事业单位工作。虽然收入不如她,但她比较稳定,看上去温柔体贴。此外,两人学历相似,老家又在江苏同一个县。在别人眼里,他们“很般配”。但是n结婚后不久,陈文汉就辞去了工作,“流转”了房子,收入微薄。两人目前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小区租房子,失业的婆婆也搬来和他们一起住,照顾孩子。 “有原则性冲突吗?比如作弊?”我像往常一样问。 “不存在作弊的情况。”小雅顿了顿,语气依然平静,“但他打了我一巴掌,因为我拒绝在他父母需要的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。而且……我觉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有问题,他总是把我的钱转到不同的名下。”他做到了吗? !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长时间,我很清楚什么是“第一次”。什么。但我也知道,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这一巴掌就决定分手。果然,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他真正关心的部分——“算账”。 “如果离婚,他能得到多少钱?” “是不是我“和解还是诉讼,哪个更便宜?”他问得清清楚楚,几乎没有任何疑问,听起来不像是在说离婚,倒像是在给当事人做风险评估。然后,她又补充道:“当然,如果我们能好好谈谈,就不需要上法庭。毕竟男孩还小,我先爱他,所以也许只是一时冲动。”他告诉我,他已经带男孩去酒店了,“我想让他冷静下来,给彼此一些空间。”在他看来,只要他立场足够坚定,陈文翰一定会来讲和,以保住他的经济来源,这件事就结束了。我看着他,心里不安。但我还是保持着专业的克制,“最好谈个交易,而且离婚的成本是最低的。”我说:“我帮你制定一个方案,回来再跟他谈谈。”他显然松了口气,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。退出。不幸的是,真正的失控才刚刚开始。半个多月后的一天,我正要睡觉时,小雅给我打电话。 “袁律师,他换锁了。”我愣了一下。谈判破裂了吗? “我回家拿东西,但门打不开。”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声音。 “他们换了锁,把我的衣服都扔在走廊里……”陈文汉的家人认为他“有脾气”。只要手段够狠,她就一定会屈服。“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住,别一个人呆着。”我的快速提醒。 “你能先发一封律师函吗?我想逼他坐下来好好谈谈。” “小雅,他并不是想这样跟你复合。”他没有拒绝,只是轻声说道:“但是我真的不想上法庭。”此时,他还在想着“掌控局势”,试图纠正翻倒的桌子。在“安全”与“尊重”之间出于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,我还是同意帮他办理离婚手续。挂了电话,我隐隐约约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有好结果。只是没想到对方的下一步动作这么快。几天后,我又接到了小雅的电话。“袁律师,帮帮我吧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,带着明显的哭声,“不管了。”我走到哪里,陈文翰就会找到我……”他的声音渐渐小了,仿佛失去了控制。“他抓起我的包,拉扯我的头发。”“他说他要把孩子扔到河里……”我坐直了身子,脑子突然清醒了。如果说过去的行为可以理解为“压力”,那么现在这简直就是恐吓。“小雅,”我打断她,“你现在在哪里? “这里安全吗?”确认他暂时安全后,我们约好在一家隐蔽的咖啡馆见面。我提前几分钟到达,坐在角落里。她的话让我们很感动。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——“无论你躲在哪里,你都会被发现。”。既然小雅故意隐藏自己,那么陈文翰又是如何一次次找上门的呢?过了一会儿,小雅到了。即使在室内,他也戴着低调的帽子和口罩。他没有立即找地方坐下,而是小心翼翼地往店门里看了一眼,然后快步走到了我的座位上。当他摘下面具时,我几乎认不出他了。他脸色苍白,眼窝深陷,眼中充满了恐惧。他看起来和以前很不一样。 “他会找到我刚刚搬家的地方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小雅问我。我猜有可能是她认识的人告诉她的? “不可能,这次转学我除了妈妈以外没有告诉任何人……”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一个看似温和的男人,怎么会突然拥有如此精准的追踪能力?在我的追问下,小雅终于透露了更多细节。原来,她在骗局时轻描淡写的一句话“因为房产证上没有写我的名字,所以被打了”,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我渐渐了解了这个家庭背后的“真面目”。小雅告诉我,结婚后,她不仅要承担家庭开支、房租、赡养公婆,还要帮忙还清丈夫老家空置的婚房贷款。她一开始并不乐意,甚至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妻子。等孩子一岁了,小雅想在南京买一套学区房。他和父母将支付大部分首付,默认情况下,房产证上会写上夫妻俩的名字。这时,公婆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要求——新房子里要加上他们的名字。理由是老家的婚房已经耗尽了家里的资金,儿子买新房加上父母的名字是“理所当然、合理的”。小雅抚养了整个家庭,她也提供超过3/4的新房。小雅无法接受,羞愧但礼貌地拒绝了。小雅说,她终于想起来了:正常的父母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?能做到gay这个要求的人,绝对不是好人。小雅的拒绝激怒了婆婆。当小雅说“把我父母的名字也加上去怎么样?”时,婆婆彻底震惊了。他指着小雅骂道:“一个女人在外面做生意,挣这么多钱是那么容易的吗?她是个贱人,一个渣男,一个伪君子……”她打累了,对着蹲在一旁的儿子喊道:“我老公不听话,你就打他吧!”随之而来的是小雅挥之不去的噩梦——高学历、一向温柔的丈夫举起手,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。瞬间,小雅就愣住了。他想不明白,为什么婆婆一句话就能让自己的丈夫打她一巴掌。婆婆看上去是一个对着她惊恐的眼神,冷冷道:“我在监狱里,什么都不怕。你要是再顽固,我就杀了你。”婆婆劝她讲和:“男人打老婆很正常,我们都在,等他老了打不了了就好了。”这时小雅终于意识到:这不是生活,这就像进入了一个黑帮,暴力被悄悄容忍,甚至被视为“家规”。在这样一帮流氓面前,讲理是没有用的。小雅决定离开家,和孩子们一起租一套新房子。为了逼对方让步,小雅生气了。断了家人的“供养”——老房子的房租不交,信用卡也停了。这一次,彻底捅了马蜂窝。那家伙的家人没有离开,没有搬家,却开始了疯狂的摊铺机。小雅上班时的手机遭到了24小时的骚扰轰炸,让她完全无法正常工作。无论他在哪里搬家——朋友家,新公寓,三天之内,陈文翰一定会像鬼一样从门外走出来。 “每次他挡住你的时候,除了用手之外,他还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吗?”我问。 “是啊!他一直抢我的手机!” “电话里有什么?” “他要转50万元到我的金融账户,还有银行卡、微信、支付宝。”这50万元理财是小雅在结婚前成功买下的。这不仅是在结婚登记之前,而且资金本身也是他和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共同拥有的。陈文汉试图将钱赎回并转入自己名下。看着宫里那个几乎被毁掉的女孩,我发现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离婚案——对方的行为很快就失控了,而小雅的状态也让我隐约担心一切随时都会变得更糟。我想要什么o不仅仅是帮小雅离婚。更紧迫的是帮助他活下去。我突然想起以前看的TVB律政剧的场景。受到骚扰和威胁的客户将申请一张纸——“个人限制令”。在中国大陆,这被称为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。这是我从事法律工作的第六个年头。与刚入行时相比,我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律师了。 2011年,我接手的第一起涉及人命的离婚案件。后来有同事半开玩笑地说,我有一种“招奇怪物的现象”,不断遇到不断超出常人想象的婚姻案例。他们一次次改变了我对关系界限的认识,小雅的事例也不例外。就在这一刻,我开始再三思考,如果有人身保护令的话,或许很多关系就不会了。不必走到最危险的一步。事实上,2008年初,地方法院就发布了人身安全保护令。虽然数量很少,但至少说明了一件事:在家里打老婆是不对的。 2015年12月27日,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,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更加正式、明确地体现在法律中。截至2017年调解,该法生效仅一年多时间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个概念还停留在电视剧里,而现实中却是一个“新物种”。一般人都看不懂,就连律师也很少能看懂。一方面,家庭暴力具有高度隐蔽性。不少当事人要么故意隐瞒,要么自欺欺人说这是“家务事”。为了尽快达到离婚的目的,他们甚至把“不报警、不闹腾”作为交换的私下条件。 “如果人们不打电话给o法院真正能处理的案件很少。更让人困惑的是,当时只有“赤条条法”,没有司法解释。程序是怎样的?保护谁,禁止谁?这一切当时都是有争议的,一切都不确定。但我很清楚,这是救小雅生命的唯一一根稻草。因为这张纸可以把陈文汉的暴行从一个侧面引出来。模糊的“家事”直接到了“违法”的红线。那一刻,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——没有同事做过,所以我没有参考资料,于是我就收集了那个男人跟踪、殴打、骚扰小雅的证据,满怀期待地交给了离婚法官,但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回应:证据不足,案件不会受理:男方的推理很现实。本来可以跟着他要p的埃斯,拖车只造成轻伤。至于那个“叫你死”的软件,没有办法证明他买过。如果没有达到发布保护令的程度,我们就会重新进行调解。路似乎被堵住了。正当我担心的时候,小雅又出事了。小雅是个很有分寸的女人,很抱歉一直打扰我。当他真正绝望的时候,他发出了求救的声音。当时我特意跟他说:“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,请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但这个承诺却让我差点崩溃。接下来的几天,我的电话就成了“热线”。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电话一接通,他就充满了呼救声:“袁律师,他又来了……”“他在敲门,我好害怕……”这种高频的恐惧,连我这个旁观者都产生了生理反应。突然我意识到:坐在办公室里看卷宗的法官永远不会忍受这种濒临崩溃的绝望。如果你不让法官亲自听,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于是,我教给小雅一个难听的方法:下次他再打她的时候,先拨打110;第二,立即拨打法官办公室的电话,电话接通后,现场语音将现场直播给法官。这一步有点像“拉伤子宫”,不太体面,不过我不在乎。另外,我还告诉小雅,我怀疑她被某种科技手段针对了,所以她应该尽量更换手机和手机SIM卡,不要把旧的带在身边。后来,小雅被要求检查他携带的所有东西,包括衣服,但是……扔掉任何他发现可疑的东西。几天后,法官也崩溃了。在回应了小雅几次颤抖甚至歇斯底里的求救声后,法官终于主动出声,语气无奈:“袁律师,请您尽快立案,如果情况属实,我们会签发这份保护令。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这个呼吸并没有持续多久——第二天,下班时间,我又接到了法官的电话。他告诉我,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另案,不属于原离婚案件的范围。由于该系统刚实施不久,审判长从未实际操作过,对流程并不熟悉。第二天早上,我又来回去法院重新提交材料。等了差不多两天,我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,通知我第二天要现场开庭。开庭前,我特意抱住小雅,对她说:“陈文翰很会演戏,不管他后面说什么,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,你是受害者,一定要表现出你的痛苦,但不要采取暴力行为。”我之所以屡次警告d 小雅开庭前是因为在前期的调解过程中,我已经对双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判断。第一次见到陈文翰,他脸圆圆的,说话不急不慢,看上去还挺老实的。很难将他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联系起来。在调解过程中,他坚持不离婚,并反复强调“我们关系很好”、“孩子还小”。但当他们私下交谈时,他却提出,如果她想离婚,就得多付钱。这种对比让我措手不及——在场面上,她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;离开现场,她反复试探底线。小雅越是情绪失控,就越是冷静和内敛,仿佛站在一旁看着她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不利的境地。相比之下,小雅却不敢在陈文翰面前正面交锋,但一旦他走进法庭,或许是觉得自己有法律支持,压抑已久的恐惧又回来了,他开始说话更容易激怒对方。当他的情绪控制住他时,他的言语就会失去分寸,变得难以听清。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但这一次我还是低估了陈文翰的下限,高估了小雅的体力。法庭外,法官还没到,陈文汉就开始尖酸刻薄,不断惹恼小雅,并扬言要绑架孩子,淹死孩子,吓唬小雅。没有一个母亲能够承受这种威胁。这一刻,小雅积攒了几个月的怨气突然爆发了。他完全忘记了我的指示。他指了指陈文翰,又指了指自己的婆婆,声音完全失控:“你以为你家人是谁?你吃了我,穿了我的东西,用了我的东西,竟然敢这样对我?”所有的委屈她一直压抑的情绪突然浮现出来。她骂他们不要脸,骂他们的家人相信她养活他们,骂那个曾经碰过她的男人——“你不是喜欢伤害人吗?当你再伤害我的时候……”他已经不在乎尊严,也不在乎后果。他本能地抛掉了所有压抑的恐惧和愤怒。殴打结束时,他的声音已经沙哑。他蹲在法院门口,抱住膝盖,放声大哭。这时,法官腋下夹着一份卷宗走了过来。这一幕准确地映入了法官的眼帘:一个侮辱妻子的歇斯底里的泼妇。结束了。我心里一痛,现在我的受害者形象彻底崩塌了。测试伊始,陈文翰就展现出了“演员级别”的演技。面对我们提交的所有无可辩驳的证据,他一脸苦涩的向法官发泄着心中的苦涩。在叙述中,她精心编织,正确而正确。两人的故事完全颠倒了:学历高、能言善辩的小雅变成了“说得对”的家霸,而她和年迈的父母却成了为了“家庭和解”而屡屡忍耐的弱势群体。他含泪指责小雅长期拿钱“补贴妈妈的弟弟”,形容自己是“老实人”,耗尽了妻子所有的积蓄,却还要忍气吞声。 “我倾尽心血,把心都给了她,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我得不到她的真心回报?”说到情感方面,这名男子竟然在法庭上哭了。当法官对这友善的坦白稍稍犹豫时,他看准了机会,扔出了真正的王牌——一张4000元的收据。小雅以前跟我提过这件事——她说有一天陈文翰前来闹事,不肯离开。他一定是在推的过程中摔坏了手机。为了解决此事,小雅认为这是“赔钱避祸”,转了4000元让他走。当时我只是把这当成一场普通的家庭纠纷,没有认真对待。没想到,这个被我忽视的“手机支付”,居然被他包装成了“家暴医疗费”,简直无敌了。这一刻,审判的叙事焦点几乎被他硬生生逆转了。我第一次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如果我几个月不跟踪案件,根据这几十分钟的对峙,我很难立即说出他到底是肇事者还是“被迫惊慌的丈夫”,更何况是一个刚接案、对双方都不熟悉的法官。看着法官的表情逐渐动摇,我几乎可以肯定,常规证据对于这样的行动是无效的。波南特。如果我们坚持既定的节奏,我们解释得越多,就越显得我们在胡闹。陈文翰的脏水还在一盆又一盆地倒着。除了偶尔惹怒小雅之外,她还常常气得放声大哭。我感觉到他轻微的下沉。如果他倒在法庭上,这个案子就很难了结,再这样下去,我们很可能会败诉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很快回忆起小雅之前告诉我的点点滴滴——他为家里付出的钱,陈文翰父亲的性格,以及那些屡次提到但从未写在笔录中的“色情传闻”。无奈之下,我想到了危险的一步——因为陈家父子坚持一个字——“钱”。他们想用金钱来定义这段婚姻,所以我也想用金钱来表明他们到底是谁。我不确定这是否有效,但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,习近平奥雅下次可能等不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,突然打断了他们,语速很快,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,也不给我反悔的时间:“西诺没良心?谁养谁?你们镇上的婚房,首付是借的,贷款也是小雅还的,房产证上写的是小雅的名字吗?” “你儿子自从认识小雅之后就没有认真工作过,交房租,还信用卡,甚至还欠亲戚的买房钱,最后还是小雅承担了责任!” “现在就因为新房不想加上你丈夫的名字,你就把她赶出家门,扔掉她的东西,还拿你的孩子来恐吓她?” “陈文翰,你是女人养大的,吃软饭的,你不觉得羞耻吗?你爸爸怂恿你打老婆,你还是个男人,还是个父亲吗?”我几乎是一口气说道。话一出口,我就感觉到了危险。面对一个很牛的人谎言暴力是一种解决办法,不知道下一秒是借口还是拳头。陈文翰本人并没有剧烈反应。他可能在律师的培训下学会了“情绪管理”。 但他的父亲先爆发了,据称是在监狱里。老爷子从礼堂里跳出来,指着小雅骂道:“你放屁!她的钱都是我儿子的钱!一个女人哪能那么容易赚到这么多钱?无耻!你在外面露脸不就是为了推销吗?!”他甚至把手指转向我。 “你这个烂律师,还靠卖钱赚到钱!你们都是贱人——”全场瞬间鸦雀无声。女店员悬在空中打字的双手停止了。我不知道法官会如何处理这件事,但我很清楚,对方的失控只是将“剑柄”握在了我们手中。我没有退缩,直接指出对方公然侮辱我们的人格、散布谣言。我要求立即复印审判视频整理证据,并明确表示要报警,将案件追查到底。听到“报警”两个字,陈文汉立刻意识到不对劲。他冲过去抓住了父亲,试图向法官解释,父亲只是一时冲动。但现在他们已经失控了。我对陈文翰说:“陈文翰,你听到了吗?你的父亲在法庭上辱骂你的妻子是‘贱人’,你同意吗?你家里是靠你所谓的‘贱人的钱’养活你的吗?” “你受过高等教育,这就是你的价值吗?” “住口!”老者彻底疯了。他冲到栏杆前,挥舞着拳头,就要打我的脸:“打你怎么了?你不听话就该打你!我也打你——”看到陈爸爸又冲进来,我猛地把小雅拉到了身后。当时,我的手心已经冒出了大汗。理性告诉我,这是一个机会——只要如果他们在法官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的真实本性,则该保护令通常会有效。但情感上,看着眼前这个眼睛发红、青筋暴起的男人,我心里真想:如果这个老头真的疯了,在法庭上对我实施暴力袭击怎么办?如果法官仍然认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家庭斗殴,并给了他们每人50拳怎么办?在这样做的过程中,我押注于我们本性对暴力的厌恶。我停止了心跳,转向法官,试图保持冷静,但音量却不知不觉地变大了:“法官,你看到了他们对小雅的真实态度。他们不仅以前多次打败过小雅,而且以后肯定还会继续遭到殴打。我请求法院立即发布保护令,避免悲剧的发生。”那一刻我真的在想,如果法官还不接受的话,我还能做什么呢?为了消除法官对偏袒任何一方的担忧,我重申保护令是只是一个“保护”屏障。只要对方不实施暴力,这张纸对他们的生活就没有真正的影响;这也让他们的当事人小雅的人身安全更加有保障。这时,陈文汉意识到父亲遇到麻烦了,连忙将父亲推回了座位上。他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,转头向法官求情:“法官,误会都是误会,是他们先惹恼了我,我父亲平时很诚实,但他就是不生气……” “你诚实吗?证据会说话。”我没有给他完成伎俩的机会,直接指着法庭上的4000元收据道出了真相:那天他分明是带人闯入小雅家闹事的。警察赶到后,他在派出所躺下翻了个身,威胁说不交钱就不站起来。小雅转账只是为了“送钱给上帝”瘟疫”。“钱来了,立刻站起来。为什么,搬家也能治病?”不等他反驳,我立刻扔出他威胁小雅的证据,问道:“小雅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,想把孩子送回奶奶家,你却说‘敢送就推到河里淹死’。陈文汉,你配得上叫爸爸吗?”法庭内,又一片寂静。法官拿起我们提交的证据,盯着被告人坐的地方:“被告人,你父亲刚刚在法庭上承认,‘如果你不听话,就会挨打’。”那么,这些证据上显示的伤势都是真的,对吧?” 陈文翰愣了一下,犹豫着辩解道:“不……这不是殴打,法官,这只是……家庭纠纷,纠纷……” 法官没有听他的解释,继续问道:“那你父亲刚才说,小雅会继续被打。”如果她将来不服从的话。这是真的吗?” “不!绝对不是!那不是打……”陈文汉仍然极力否认。最后,法官说道:“好吧,鉴于你刚才的表现以及已经发生的事实,我认为这个保护令是有必要的。至少可以让大家冷静下来……” “冷静干什么?!” 法官还没说完,陈文汉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,指着法官的鼻子威胁道:“这份保护令你不能签!如果你敢发出保护令,我不会解雇你。我天天上法庭闹事!”他的父亲也站起来说道:“就是啊!我为什么要这样做?会给我儿子带来不好的名声!何况,他还应该被打!”这时,法官怒笑起来,一边飞快地整理着卷宗,一边冷冷地说道:“被告人,我到了最后一刻还在犹豫。但现在,你们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了,我必须发出这份抗议书。行动命令!休庭!”这一次,刚才还生气的父子俩终于意识到“不对劲了。”他们留在蜂巢上不肯离开,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话试图赔罪:“法官,你刚才生气了,我并没有真正伤害他……”法官头也不抬,只是摆摆手:“保护令只是一纸空文。陈文汉的家人被法警请来了。我经过的时候,听到刚刚痛哭流涕的男子低声嘀咕:“赚两块钱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”在他看来,小雅不是一个“伤害者”,而是一个“犯了错误需要纠正的人”。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在门外,法官才缓缓向我们走来:“袁律师,我今天就做出保护令的决定,明天就可以拿到了。”直到这一刻,小雅才真正明白了。恢复。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紧张的情绪彻底放松,她又放声大哭起来。法官看了看小雅,又看了看我,叹了口气。怒:“袁律师,你真是勇敢啊,今天老夫冲你冲过来的时候,你不害怕吗?” “害怕的。”我看着还在颤抖的小雅,苦笑了一下。我的腿确实软了,“但我更怕小雅会死。”小雅哭着发泄痛苦,法官补充道:“以后让你的当事人管住那张嘴吧,他骂得太过分了,如果你现在不露出他的真面目,我真怀疑他‘活该’。”从法庭出来时,阳光相当刺眼。虽然这场战斗我赢了,但我心里的阴云却没有消失。刚才陈文翰的咕哝声让我有些不安。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。按照他的逻辑,小雅不听话,想要离婚。这是挑衅。所以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实施暴力,他觉得自己是在“管理自己的行为”。就在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,路边的树后突然出现了两个黑影——陈文翰父子并没有离开。法官都下达了保护令,你还敢伤人?!我一边喊着,一边用身体护着瘦弱的小雅,往法院保卫室的方向退去。“等你来拿!”陈文翰一脸怒气冲冲地说。幸好路边有出租车站。我赶紧把小雅放进车里,小雅看到我独自面对着陈家人和她的儿子,她想下车面对他们。帮帮小雅,还是我把自己推过去边缘?如果法官今天不生气怎么办?如果保护令不起作用怎么办?但我发现我别无选择。因为每当我犹豫的时候,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小雅哭着说的“袁律师,救救我”。有些案件只有在您准备好后才会受理。你就站在那儿,别无选择。那天以后,我坚持每次开庭都要请法官让我们走十分钟,并请法警护送我们。于是,在随后的每次法庭审理中,都出现了民事诉讼中罕见的“法警值班”的情况。每次审完后,法警都会拦住他们,让我们先离开。即便如此,我们也一度在法庭外被亲属包围、辱骂……终于,来之不易的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下达了。看到这个决定,我和小雅都松了一口气。现在有了这个法盾,我终于可以挡住小雅面对的拳头了。 拿到保护令后的最初几天,夏阿弥仍不敢放松。他担心地问我:“袁律师,这篇论文真的有用吗?他真的不回来了吗?”我当时满怀信心地安慰她:“放心吧,这是朝廷的命令,他要是敢违背,后果是他承担不起的。”此后,陈文汉冷静了一会儿。他偶尔会出现在小雅的工作场所几次,但小雅报警后就逃跑了。与此同时,他也再也没有出现在小雅的住处附近。几个月过去了。小雅慢慢放下了警惕,开始相信我的话——她安全了。可谁也没想到,当我们都以为是时候翻过这一页的时候,陈文翰却回来了。四个多月后的一天,小雅突然给我发了一些照片。点开大图的那一刻,我的心猛地一跳,感到一阵寒意。那是他的体检照片,他的头皮上有一块秃了,头发被拔掉了很多,他的手臂也被拔掉了。身上布满了血淋淋的划痕。当晚,他下班后就直接叫了一辆网约车。上车前距离单位门口仅十几米。早已等候多时的陈文汉突然带着一群亲人冲了过来,将他团团围住。小雅奋力逃脱,上了车。陈文汉在车上追赶并殴打了他。路人想要打架,结果却把小雅从车里拉了出来,拖到了地上。光是看照片,我就已经感受到了痛苦和绝望。我既愤怒又内疚。令他愤怒的是,这个家庭无法无天;让她感到内疚的是,是我告诉她“有了保护令,她就会安全”。现在这些伤口,虽然我没有,但感觉就像是被人打在脸上一样。我立即收集了所有证据,再次向法院申请:陈文汉严重违反保护令,必须入狱!我本以为这笔交易很划算,结果却被法官泼了一盆冷水。拒绝拘留。很现实,法官的解释也很严厉:“袁律师,他态度不好。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,你们还在离婚诉讼中,你们还有孩子,如果他坐牢15天,第16天就出来了怎么办?如果他打碎罐子,用刀刺伤人,或者伤害别人,后果谁来承担?”我张了张嘴想要反驳,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今天回想起来,保护令制度确实具有强大的威慑力。现在的保护范围不仅限于虐待、恐吓、间谍活动,更重要的是,如果被告胆敢违反禁令,情节严重的,将被定罪入狱。但当时的规则并不像今天那么明确。法官的担忧也是现实的。这是当前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司法——我们要用法律来惩罚不法分子,但也要注意不要“让不法分子太愤怒”。听起来很荒唐,但是为了当事人的生命,我们也只能承受。最终,法院依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对这一严重暴力行为处以1000元罚款。收到决定的那天,我感觉那张纸很轻,却很沉重,令人窒息。 1000元。这就是一个女人当街剪发、尊严被践踏所付出的代价吗?与此同时,我也接到了对方律师的电话。他的语气很专业,带着审慎的鼓励:“袁律师,我们都是代理人,办案的时候,不要过多地卷入当事人的情感纠葛。”我回答:“不是,我们是在事实和证据上讨论。” “我就直说吧,”他突然语气一变,“袁律师,你的委托人太卑鄙了。”我愣了一下,没想到同事之间都会使用这样的话。他继续表达自己的偏见:“你看看审判前的他,那一刻他像泼妇一样咒骂,全程嚣张,这种人……”那一刻,我再次感受到了悲伤的“完美受害者”逻辑。在他们眼里,小雅被打、被威胁,哭不出来,闹不出来。只要她破坏、战斗,她就成了“傻子”,送妻子去医院的男人,就成了被狡猾欺负的老实人——注意说话。 “律师。我冷冷地打断她的话,“我比你更清楚我的委托人是什么样的人。按照你的说法,应该在家打她才对吧?”挂断电话后,我叹了口气,压下了心中的怒火。这次谈话我没有告诉小雅。在整个案件中,她已经受够了冷眼和偏见,我不想让她知道,即使拿到了法律文件,偏见依然如山。仍然在那里。那个时候,小雅的整个人格也随之思考,变得安静……有一天,她也安静了。我疯了吗? ” 我愣了一下,她低下头,声音很轻,“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本来就很受人尊敬。 ”她说,最近她照镜子时,看到里面那个衣衫不整、紧张的女人,她感到很震惊。“有时候我在想,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?如果不是,他为什么盯着我?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不是抱怨,而是认真思考。这就是我最不舒服的地方——她明明是受害者,却迫使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“罪有应得”。我知道单靠安慰是没有用的。如果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,我们不能等他打,我们必须主动出击。‘房子的事’,受害者没有办法回转;当法律最终介入时,恶人之前的“家事”让他得以逍遥法外,这次我不得不砍掉这个“家事”的遮羞布。当晚,我独自坐在办公室,把这几个月来的案卷、记录、证据材料全部摆在桌子上,决定从头到尾仔细过一遍,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。这次筛选,确实让我抓住了之前忽略的“致命点”。在之前的庭审中,我只认为这是“敲诈勒索的证据”,以证明该男子是无赖。我立即联系小雅,了解当天除了4000块钱,小雅在她心里只是简单地称之为“被推翻”的民事纠纷,但在我看来,这是一起被压制的“家事”。立案? ! “我几乎增长了多少世界末日。 “警察来了,但我母亲已经被救护车带走了。”小雅低着头,声音颤抖着,“陈文涵就躺在派出所里翻来覆去,说被邻居打了,不交医药费就起不来。警察见卡那副凶恶的样子,形容这是‘互相打架’,建议调解。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着我妈,只想着把她从我身边赶走,而我妈要的就是我。我就转学了。”私下4000元……”最致命的是,小雅此时并不知道这可能是刑事犯罪,并申请损害赔偿。她错过了整理证据的黄金窗口,现在才能回到冰冷的病历中。小雅还表示,后来陈文涵还打伤了她的哥哥,她的弟弟也回应称这是家里的事情。那一刻,我气得想把桌子打碎,但我又焦急万分。我们说我不能说话。通过这些细节,我再次看到了小雅的致命弱点——她并不软弱,她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邪恶。当陈文汉带着一群人去敲门时,小雅妈妈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。相反,他下意识地想要保持尊严,甚至邀请他们坐下来吃饭,试图“好好谈谈”。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善良、通情达理。从事法律工作这些年,我见过很多坏人和坏事,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为受害者感到心痛。了解了来龙去脉后,我立即指示小雅:即使当时没有身份,所有的报警记录和医院记录也必须拿到。只要打人的事实存在,只要医生记录了造成的伤害,他就不能忽视。这4000元不是赔偿,ngunit“故意伤害”铁证如山!请妈妈再次报警,详细描述事件,并坚持进行损害评估。如果创伤不可见,则可以使用当时的医疗记录和影像数据。在审查证据的过程中,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——该男子的支付宝票据是对方律师在申请保护令前两天发送的。初衷是为了管理家庭开支。在拥挤的支付流程中,我发现了两份几乎不起眼的订单——一套“叫死你”软件和一些“微键GPS定位器”。该追踪器的购买页面明确注明“用于间谍用途,待机时间太长”。那一刻,一切终于明白了。微型定位器很可能原本藏在小雅的随身物品中或者汽车的角落里。难怪小雅之前换过手机和卡,但是都不起作用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人身保护令下达后的几个月里,陈文汉只能去工作单位寻找小雅。并不是因为他突然害怕了法律,而是因为我让小雅把他的东西彻底清理干净,不小心切断了他的追踪信号。不是他不想在家里闹事,而是他找不到小雅的家。既然你习惯了躲在黑暗中射出冷箭,这次我就要把你拉到阳光下,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这又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拉锯战。尽管伤势严重、证据可信,但当时办案机构仍倾向于将其视为“斗殴事件”。我们的刑事起诉一次又一次碰壁。关键时刻,保护令成功。有了这个“官方背书”,侦查人员对案件性质的判断终于发生了改变,侦查速度也大大加快。最终,正义迟来却又到来——法院判决陈文涵有罪f“故意伤害”,判处9个月监禁;他的母亲被判处7个月监禁。这句话,让陈文翰的父亲毫发无伤。因为公安调查,他在电话里给我打电话求饶,他说只要小雅撤回指控,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,他同意立即离婚,放弃监护权,甚至不要求分割小雅婚前财产76万元。当我不肯放手的时候,他又提出了一个可笑的要求:能把所有的罪孽都交给他吗?如果不是看到这一家人的面容,我差点就会被这个“孝子”所吸引。在电话里,我严格告知他:作为一名律师,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忠实地转达给委托人,绝对不存在任何私人干涉的可能。不存在“撤销”刑事指控的说法。如果您确实想谈论调解,请带您的律师去警察局虱子站正式处理事情。若有达成协议,则要看办案机构是否同意。这绝对不是我们私下可以做的事情。陈文翰见我不帮忙,又继续说道:“袁律师,你们律师不是总是‘吃原告吃被告’吗,这样你也可以帮我,我也可以付钱给你……”我直接打断他:“既然立案了,那就交给法律吧。”吃原告,吃被告——他认为是律师最大的误会,作为与我和解的筹码。或许在他这样的人眼里,只要把钱摆上台面,就能收买所有人的良心。陈文汉见我完全拒绝,又恢复原状,在电话里咒骂我和小雅。我没理他,挂了电话。到头来,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他和他顺从的母亲。在这个宗法家庭里,父亲是皇帝,儿子是太子,母亲是皇帝。她只是一颗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。在陈文涵被立案并再次延长保护令的同时,小雅的离婚诉讼进展非常顺利,案件很快就结案了。小雅拿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和应得的财产,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 一年多后,小雅的微信再次点亮了我的手机。我以为它是在向我介绍一家企业,但当我点击它时,它又请求帮助。原来,陈文翰刑满释放。这次他学得不错,没有直接行动,而是了解到“人是恶心的”。他以“要求减少子女抚养费”为由,在数百公里外的家乡起诉了小雅,并申请冻结账户。小雅被迫离开,返回家乡应诉,但开庭当天,陈文翰并没有到场。法院驳回上诉e.但一个月后,他再次提起诉讼。这种“狼来了”的游戏他永远玩不厌。那时候,小雅最害怕的就是手机响了。当她看到法庭传票的时候,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犹豫了很久,他给我打电话,询问是否可以委托我回老家应诉。听了他的描述,我松了一口气。只要不是暴力伤害,这种无赖的伎俩在我眼里就是幼稚的。 “小雅,你没必要为了这种小事花钱请律师。”我告诉他:“但是这一次,你必须自己让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低声问道:“真的……可以吗?只有我吗?”我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教他整理好所有传票和居住证明,并写了一份《管辖权异议申请书》和一封向法院申诉的信。信中只强调了一点t:原告恶意利用庭审过程,多次提起诉讼、无故缺席,对被告进行骚扰。材料寄出没几天,小雅就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——不是管辖权异议,而是男子撤诉。他把截图发给我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:“袁律师,看来他这次不闹了。”我知道对于西奥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打赢官司。但他第一次发现,自己不需要躲在律师后面,他也可以打倒坏人。生活似乎终于回到了正轨。不幸的是,坏人不会那么轻易停止。 2023年冬天的一天,离婚六年后,陈文翰裹紧自己,走进了小雅的小区。恐惧是有记忆的。尽管他刻意遮住了脸,小雅还是从猫眼里认出了他,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陈文翰徘徊在门,用猫眼擦着脖子。警察来了,他就逃跑;警察来了,他就逃跑。当警察离开时,他会以鬼魂的形式重新出现。即便是偶尔,他也有一套说法——他来看望孩子们,不打架,不打人,不跟居民闹事。警察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阻止他们。他还开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“君子报仇不晚”之类的疯狂言论,截图很快就发给了小雅。面对这种“不违法但卑鄙”的骚扰,常规方法实在是无效。 “袁律师,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他吗?”小雅的声音里透着许久未见的无奈。 “既然他不遵守武德,那我们就用魔法来战胜魔法吧。”我让小雅把陈文涵的照片、朋友圈截图、那个人的保护令、离婚判决书、刑事定罪书都拍下来,直接放到网上经理的办公桌。 “你看清楚,这家伙有严重的暴力前科,在监狱里,现在天天在小区里闲逛哦,如果再允许他,如果有人被杀了……”小雅看着经理的眼睛,一字一顿地说,“你们物业公司是第一责任人,物业的态度并不积极,他们用一种有些责备的方式解释道:“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,大家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……”但这一次,小雅没有退缩。他自己打印了数十张告示,上面贴有陈文汉的照片和判决书截图,并称:“此人态度暴力。请业主注意安全。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,工作人员应立即报警。”他要求物业公司将这些告示张贴在门禁和电梯入口处,否则他将拒绝支付物业费并向Houseiof和Urb投诉an-农村发展局。从那天起,社区治安就加强了。陈文翰已经无法再潜入社区了。由于无法进入小区,陈文汉将目标瞄准了孩子们。孩子放学了。幸好有路人拦住了他,才没让他得逞。然后,小雅给我打电话,几乎浑身发抖。我让她带孩子去医院做心理评估,并申请暂停探视权。但在法庭上,陈文翰依然展现出了父爱。当法官问男孩是否想见父亲时,男孩只说了一句话:“爸爸太可怕了。” “那不是指责,那是一种本能。暂停访问的决定来得很快。小雅告诉我,她真的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避开坏人。一年后,2024年的某一天,我的手机再次震动,“小雅”的名字在屏幕上跳动。我的心突然一沉,一种熟悉的预感袭上心头。我……当即离开会议室,深吸一口气,吸了一口气。 “喂,袁律师……”电话那头小雅的声音有些犹豫。我握紧了电话:“别怕,她是不是又搞事情了?”不,不是!小雅说她有了新男友,想咨询再婚的法律问题。他说,这一次,他要认真地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听着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未来的打算,我突然意识到——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求助了。挂断电话后,我站在窗前,良久没有动。多年来,我陪伴他经历了报警、取证、立案、庭审、量刑、事后处理等过程。缓解骚扰,每一步的防御和攻击。每一步都不高贵,也不轻松,甚至不能称之为“胜利”。我们只是坚持住,把他从“快要被拉回来”的边缘拉了回来。但现在,他终于不用依靠这些方法来确认自己是否安全了。直到这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,有时法律是非常缓慢和有限的。它不能使一个人再次完整,不能消除恐惧,不能保证没有痛苦的生活。但经过反复使用,却可以为一个即将被吞噬的人守住底线,不至于被拖回最黑暗的深渊。而正是底线让人们有机会再活一次。每当网络上出现家暴新闻,评论区总会出现一些看似合理的问题——“为什么不报警?”“为什么不离婚?”“肯定是一个准备打架,一个准备受苦了。”“这些话看似简单,实则不多。”人们真正设身处地地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:当恐惧、怀疑和优柔寡断使一步比另一步更难自己迈出的时候。袁律师表示,这些年来,法律逐渐发展起来。财产规则更加明确,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更加明确。很多系统的发展看似前进了一小步,但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处境——比如最终被更多人认识并开始实际使用的人身安全防护令。正是在这些变化中,他逐渐意识到系统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。当它真正被激活时,可以为陷入困境的人争取一些喘息的空间,甚至一条出路。但在她遇到的客户中,亲密关系破裂时的优柔寡断、焦虑和旧病复发几乎从未消失过。他见过不断回来咨询但无法想象离开的客户;他还看到了更多看似平静但慢慢崩溃为长期消耗的关系。因此,在这个系列中,他更愿意记录的不仅仅是输赢和结果,而是这十年来人们如何逐渐理解婚姻、界限和“离开”这件事。通过关注本系列,您将看到真实的故事被看到和理解,并且选择的负担不必由所涉及的人独自承担。 (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)编辑:岳半明蒸蛋配插画:大乌花
特别声明:以上内容(如有,包括照片或视频)由自媒体平台“网易号”用户上传发布。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。
注:以上内容(包括图片和视频,如有)由网易号用户上传发布,网易号为社交媒体平台,仅提供存储服务信息。
大家好,我是陈卓。最精彩的案件不是刑事案件,而是婚姻案件。 “这不是我说的,”我刚认识的一位新律师说。他的名字叫袁劲松。他说,在法律界,有人求财,有人求名。他不仅喜欢这些东西,还喜欢“自找麻烦”。他热衷于处理他能接手的最奇怪的离婚案件。我问怎么奇怪,他说反正比国产电视剧更荒唐。 “上帝是最好的编剧,但当他写关于人类婚姻的章节时,他一定是喝醉了。” 2011年,当他刚入行时,他心里就意识到了这一点,因为他接手的第一起离婚案涉及三个人的生命——两个人被谋杀,一个被判处死刑。这是她的婚姻案件第一次超出了普通人对离婚纠纷的想象。在这种情况下,客户发给他的消息是这样开头的——“法律叶媛,救救我。” “他又来了……” “他在敲门。我好害怕……”后来,他接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件,涉及欺骗、控制、彩礼、算计、暴力。它们伪装成家居用品,但往往变成了奇观。委托人害怕这些困难,也害怕面对离婚后的生活。在处理这些奇怪的人、奇怪的事时,他经常准备自己的金嗓子含片,因为无论是保护委托人,还是与对方律师争论,他的声音必须是美丽的。现在,袁劲桑决定把这个系列的故事叫做《奇怪的婚姻中介》,他想要记录的不仅仅是输赢,而是让更多的人站在第三者的角度,看清婚姻中的奇葩,避免伤害,理性地去爱,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,我几乎不会记得第一次见到小雅的情景。2017年深秋,我刚刚结束庭审,第一次见到了小雅。和大多数金融白领一样,她化着精致的妆容,穿着考究的衣服,坐着时背部挺直。他看起来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,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“袁律师,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的事情。”一如既往,我询问了主要情况:小雅,28岁,名校毕业,在当地一家金融机构担任业务骨干;她的丈夫陈文翰与她同岁,也是名校毕业,是她的初恋情人。他们结婚才一年多。婚前,陈文翰在事业单位工作。虽然收入不如她,但她比较稳定,看上去温柔体贴。此外,两人学历相似,老家又在江苏同一个县。在别人眼里,他们“很般配”。但是n结婚后不久,陈文汉就辞去了工作,“流转”了房子,收入微薄。两人目前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小区租房子,失业的婆婆也搬来和他们一起住,照顾孩子。 “有原则性冲突吗?比如作弊?”我像往常一样问。 “不存在作弊的情况。”小雅顿了顿,语气依然平静,“但他打了我一巴掌,因为我拒绝在他父母需要的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。而且……我觉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有问题,他总是把我的钱转到不同的名下。”他做到了吗? !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长时间,我很清楚什么是“第一次”。什么。但我也知道,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这一巴掌就决定分手。果然,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他真正关心的部分——“算账”。 “如果离婚,他能得到多少钱?” “是不是我“和解还是诉讼,哪个更便宜?”他问得清清楚楚,几乎没有任何疑问,听起来不像是在说离婚,倒像是在给当事人做风险评估。然后,她又补充道:“当然,如果我们能好好谈谈,就不需要上法庭。毕竟男孩还小,我先爱他,所以也许只是一时冲动。”他告诉我,他已经带男孩去酒店了,“我想让他冷静下来,给彼此一些空间。”在他看来,只要他立场足够坚定,陈文翰一定会来讲和,以保住他的经济来源,这件事就结束了。我看着他,心里不安。但我还是保持着专业的克制,“最好谈个交易,而且离婚的成本是最低的。”我说:“我帮你制定一个方案,回来再跟他谈谈。”他显然松了口气,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。退出。不幸的是,真正的失控才刚刚开始。半个多月后的一天,我正要睡觉时,小雅给我打电话。 “袁律师,他换锁了。”我愣了一下。谈判破裂了吗? “我回家拿东西,但门打不开。”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声音。 “他们换了锁,把我的衣服都扔在走廊里……”陈文汉的家人认为他“有脾气”。只要手段够狠,她就一定会屈服。“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住,别一个人呆着。”我的快速提醒。 “你能先发一封律师函吗?我想逼他坐下来好好谈谈。” “小雅,他并不是想这样跟你复合。”他没有拒绝,只是轻声说道:“但是我真的不想上法庭。”此时,他还在想着“掌控局势”,试图纠正翻倒的桌子。在“安全”与“尊重”之间出于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,我还是同意帮他办理离婚手续。挂了电话,我隐隐约约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有好结果。只是没想到对方的下一步动作这么快。几天后,我又接到了小雅的电话。“袁律师,帮帮我吧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,带着明显的哭声,“不管了。”我走到哪里,陈文翰就会找到我……”他的声音渐渐小了,仿佛失去了控制。“他抓起我的包,拉扯我的头发。”“他说他要把孩子扔到河里……”我坐直了身子,脑子突然清醒了。如果说过去的行为可以理解为“压力”,那么现在这简直就是恐吓。“小雅,”我打断她,“你现在在哪里? “这里安全吗?”确认他暂时安全后,我们约好在一家隐蔽的咖啡馆见面。我提前几分钟到达,坐在角落里。她的话让我们很感动。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——“无论你躲在哪里,你都会被发现。”。既然小雅故意隐藏自己,那么陈文翰又是如何一次次找上门的呢?过了一会儿,小雅到了。即使在室内,他也戴着低调的帽子和口罩。他没有立即找地方坐下,而是小心翼翼地往店门里看了一眼,然后快步走到了我的座位上。当他摘下面具时,我几乎认不出他了。他脸色苍白,眼窝深陷,眼中充满了恐惧。他看起来和以前很不一样。 “他会找到我刚刚搬家的地方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小雅问我。我猜有可能是她认识的人告诉她的? “不可能,这次转学我除了妈妈以外没有告诉任何人……”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一个看似温和的男人,怎么会突然拥有如此精准的追踪能力?在我的追问下,小雅终于透露了更多细节。原来,她在骗局时轻描淡写的一句话“因为房产证上没有写我的名字,所以被打了”,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我渐渐了解了这个家庭背后的“真面目”。小雅告诉我,结婚后,她不仅要承担家庭开支、房租、赡养公婆,还要帮忙还清丈夫老家空置的婚房贷款。她一开始并不乐意,甚至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妻子。等孩子一岁了,小雅想在南京买一套学区房。他和父母将支付大部分首付,默认情况下,房产证上会写上夫妻俩的名字。这时,公婆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要求——新房子里要加上他们的名字。理由是老家的婚房已经耗尽了家里的资金,儿子买新房加上父母的名字是“理所当然、合理的”。小雅抚养了整个家庭,她也提供超过3/4的新房。小雅无法接受,羞愧但礼貌地拒绝了。小雅说,她终于想起来了:正常的父母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?能做到gay这个要求的人,绝对不是好人。小雅的拒绝激怒了婆婆。当小雅说“把我父母的名字也加上去怎么样?”时,婆婆彻底震惊了。他指着小雅骂道:“一个女人在外面做生意,挣这么多钱是那么容易的吗?她是个贱人,一个渣男,一个伪君子……”她打累了,对着蹲在一旁的儿子喊道:“我老公不听话,你就打他吧!”随之而来的是小雅挥之不去的噩梦——高学历、一向温柔的丈夫举起手,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。瞬间,小雅就愣住了。他想不明白,为什么婆婆一句话就能让自己的丈夫打她一巴掌。婆婆看上去是一个对着她惊恐的眼神,冷冷道:“我在监狱里,什么都不怕。你要是再顽固,我就杀了你。”婆婆劝她讲和:“男人打老婆很正常,我们都在,等他老了打不了了就好了。”这时小雅终于意识到:这不是生活,这就像进入了一个黑帮,暴力被悄悄容忍,甚至被视为“家规”。在这样一帮流氓面前,讲理是没有用的。小雅决定离开家,和孩子们一起租一套新房子。为了逼对方让步,小雅生气了。断了家人的“供养”——老房子的房租不交,信用卡也停了。这一次,彻底捅了马蜂窝。那家伙的家人没有离开,没有搬家,却开始了疯狂的摊铺机。小雅上班时的手机遭到了24小时的骚扰轰炸,让她完全无法正常工作。无论他在哪里搬家——朋友家,新公寓,三天之内,陈文翰一定会像鬼一样从门外走出来。 “每次他挡住你的时候,除了用手之外,他还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吗?”我问。 “是啊!他一直抢我的手机!” “电话里有什么?” “他要转50万元到我的金融账户,还有银行卡、微信、支付宝。”这50万元理财是小雅在结婚前成功买下的。这不仅是在结婚登记之前,而且资金本身也是他和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共同拥有的。陈文汉试图将钱赎回并转入自己名下。看着宫里那个几乎被毁掉的女孩,我发现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离婚案——对方的行为很快就失控了,而小雅的状态也让我隐约担心一切随时都会变得更糟。我想要什么o不仅仅是帮小雅离婚。更紧迫的是帮助他活下去。我突然想起以前看的TVB律政剧的场景。受到骚扰和威胁的客户将申请一张纸——“个人限制令”。在中国大陆,这被称为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。这是我从事法律工作的第六个年头。与刚入行时相比,我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律师了。 2011年,我接手的第一起涉及人命的离婚案件。后来有同事半开玩笑地说,我有一种“招奇怪物的现象”,不断遇到不断超出常人想象的婚姻案例。他们一次次改变了我对关系界限的认识,小雅的事例也不例外。就在这一刻,我开始再三思考,如果有人身保护令的话,或许很多关系就不会了。不必走到最危险的一步。事实上,2008年初,地方法院就发布了人身安全保护令。虽然数量很少,但至少说明了一件事:在家里打老婆是不对的。 2015年12月27日,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,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更加正式、明确地体现在法律中。截至2017年调解,该法生效仅一年多时间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个概念还停留在电视剧里,而现实中却是一个“新物种”。一般人都看不懂,就连律师也很少能看懂。一方面,家庭暴力具有高度隐蔽性。不少当事人要么故意隐瞒,要么自欺欺人说这是“家务事”。为了尽快达到离婚的目的,他们甚至把“不报警、不闹腾”作为交换的私下条件。 “如果人们不打电话给o法院真正能处理的案件很少。更让人困惑的是,当时只有“赤条条法”,没有司法解释。程序是怎样的?保护谁,禁止谁?这一切当时都是有争议的,一切都不确定。但我很清楚,这是救小雅生命的唯一一根稻草。因为这张纸可以把陈文汉的暴行从一个侧面引出来。模糊的“家事”直接到了“违法”的红线。那一刻,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——没有同事做过,所以我没有参考资料,于是我就收集了那个男人跟踪、殴打、骚扰小雅的证据,满怀期待地交给了离婚法官,但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回应:证据不足,案件不会受理:男方的推理很现实。本来可以跟着他要p的埃斯,拖车只造成轻伤。至于那个“叫你死”的软件,没有办法证明他买过。如果没有达到发布保护令的程度,我们就会重新进行调解。路似乎被堵住了。正当我担心的时候,小雅又出事了。小雅是个很有分寸的女人,很抱歉一直打扰我。当他真正绝望的时候,他发出了求救的声音。当时我特意跟他说:“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,请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但这个承诺却让我差点崩溃。接下来的几天,我的电话就成了“热线”。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电话一接通,他就充满了呼救声:“袁律师,他又来了……”“他在敲门,我好害怕……”这种高频的恐惧,连我这个旁观者都产生了生理反应。突然我意识到:坐在办公室里看卷宗的法官永远不会忍受这种濒临崩溃的绝望。如果你不让法官亲自听,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于是,我教给小雅一个难听的方法:下次他再打她的时候,先拨打110;第二,立即拨打法官办公室的电话,电话接通后,现场语音将现场直播给法官。这一步有点像“拉伤子宫”,不太体面,不过我不在乎。另外,我还告诉小雅,我怀疑她被某种科技手段针对了,所以她应该尽量更换手机和手机SIM卡,不要把旧的带在身边。后来,小雅被要求检查他携带的所有东西,包括衣服,但是……扔掉任何他发现可疑的东西。几天后,法官也崩溃了。在回应了小雅几次颤抖甚至歇斯底里的求救声后,法官终于主动出声,语气无奈:“袁律师,请您尽快立案,如果情况属实,我们会签发这份保护令。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这个呼吸并没有持续多久——第二天,下班时间,我又接到了法官的电话。他告诉我,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另案,不属于原离婚案件的范围。由于该系统刚实施不久,审判长从未实际操作过,对流程并不熟悉。第二天早上,我又来回去法院重新提交材料。等了差不多两天,我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,通知我第二天要现场开庭。开庭前,我特意抱住小雅,对她说:“陈文翰很会演戏,不管他后面说什么,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,你是受害者,一定要表现出你的痛苦,但不要采取暴力行为。”我之所以屡次警告d 小雅开庭前是因为在前期的调解过程中,我已经对双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判断。第一次见到陈文翰,他脸圆圆的,说话不急不慢,看上去还挺老实的。很难将他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联系起来。在调解过程中,他坚持不离婚,并反复强调“我们关系很好”、“孩子还小”。但当他们私下交谈时,他却提出,如果她想离婚,就得多付钱。这种对比让我措手不及——在场面上,她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;离开现场,她反复试探底线。小雅越是情绪失控,就越是冷静和内敛,仿佛站在一旁看着她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不利的境地。相比之下,小雅却不敢在陈文翰面前正面交锋,但一旦他走进法庭,或许是觉得自己有法律支持,压抑已久的恐惧又回来了,他开始说话更容易激怒对方。当他的情绪控制住他时,他的言语就会失去分寸,变得难以听清。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但这一次我还是低估了陈文翰的下限,高估了小雅的体力。法庭外,法官还没到,陈文汉就开始尖酸刻薄,不断惹恼小雅,并扬言要绑架孩子,淹死孩子,吓唬小雅。没有一个母亲能够承受这种威胁。这一刻,小雅积攒了几个月的怨气突然爆发了。他完全忘记了我的指示。他指了指陈文翰,又指了指自己的婆婆,声音完全失控:“你以为你家人是谁?你吃了我,穿了我的东西,用了我的东西,竟然敢这样对我?”所有的委屈她一直压抑的情绪突然浮现出来。她骂他们不要脸,骂他们的家人相信她养活他们,骂那个曾经碰过她的男人——“你不是喜欢伤害人吗?当你再伤害我的时候……”他已经不在乎尊严,也不在乎后果。他本能地抛掉了所有压抑的恐惧和愤怒。殴打结束时,他的声音已经沙哑。他蹲在法院门口,抱住膝盖,放声大哭。这时,法官腋下夹着一份卷宗走了过来。这一幕准确地映入了法官的眼帘:一个侮辱妻子的歇斯底里的泼妇。结束了。我心里一痛,现在我的受害者形象彻底崩塌了。测试伊始,陈文翰就展现出了“演员级别”的演技。面对我们提交的所有无可辩驳的证据,他一脸苦涩的向法官发泄着心中的苦涩。在叙述中,她精心编织,正确而正确。两人的故事完全颠倒了:学历高、能言善辩的小雅变成了“说得对”的家霸,而她和年迈的父母却成了为了“家庭和解”而屡屡忍耐的弱势群体。他含泪指责小雅长期拿钱“补贴妈妈的弟弟”,形容自己是“老实人”,耗尽了妻子所有的积蓄,却还要忍气吞声。 “我倾尽心血,把心都给了她,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我得不到她的真心回报?”说到情感方面,这名男子竟然在法庭上哭了。当法官对这友善的坦白稍稍犹豫时,他看准了机会,扔出了真正的王牌——一张4000元的收据。小雅以前跟我提过这件事——她说有一天陈文翰前来闹事,不肯离开。他一定是在推的过程中摔坏了手机。为了解决此事,小雅认为这是“赔钱避祸”,转了4000元让他走。当时我只是把这当成一场普通的家庭纠纷,没有认真对待。没想到,这个被我忽视的“手机支付”,居然被他包装成了“家暴医疗费”,简直无敌了。这一刻,审判的叙事焦点几乎被他硬生生逆转了。我第一次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如果我几个月不跟踪案件,根据这几十分钟的对峙,我很难立即说出他到底是肇事者还是“被迫惊慌的丈夫”,更何况是一个刚接案、对双方都不熟悉的法官。看着法官的表情逐渐动摇,我几乎可以肯定,常规证据对于这样的行动是无效的。波南特。如果我们坚持既定的节奏,我们解释得越多,就越显得我们在胡闹。陈文翰的脏水还在一盆又一盆地倒着。除了偶尔惹怒小雅之外,她还常常气得放声大哭。我感觉到他轻微的下沉。如果他倒在法庭上,这个案子就很难了结,再这样下去,我们很可能会败诉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很快回忆起小雅之前告诉我的点点滴滴——他为家里付出的钱,陈文翰父亲的性格,以及那些屡次提到但从未写在笔录中的“色情传闻”。无奈之下,我想到了危险的一步——因为陈家父子坚持一个字——“钱”。他们想用金钱来定义这段婚姻,所以我也想用金钱来表明他们到底是谁。我不确定这是否有效,但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,习近平奥雅下次可能等不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,突然打断了他们,语速很快,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,也不给我反悔的时间:“西诺没良心?谁养谁?你们镇上的婚房,首付是借的,贷款也是小雅还的,房产证上写的是小雅的名字吗?” “你儿子自从认识小雅之后就没有认真工作过,交房租,还信用卡,甚至还欠亲戚的买房钱,最后还是小雅承担了责任!” “现在就因为新房不想加上你丈夫的名字,你就把她赶出家门,扔掉她的东西,还拿你的孩子来恐吓她?” “陈文翰,你是女人养大的,吃软饭的,你不觉得羞耻吗?你爸爸怂恿你打老婆,你还是个男人,还是个父亲吗?”我几乎是一口气说道。话一出口,我就感觉到了危险。面对一个很牛的人谎言暴力是一种解决办法,不知道下一秒是借口还是拳头。陈文翰本人并没有剧烈反应。他可能在律师的培训下学会了“情绪管理”。 但他的父亲先爆发了,据称是在监狱里。老爷子从礼堂里跳出来,指着小雅骂道:“你放屁!她的钱都是我儿子的钱!一个女人哪能那么容易赚到这么多钱?无耻!你在外面露脸不就是为了推销吗?!”他甚至把手指转向我。 “你这个烂律师,还靠卖钱赚到钱!你们都是贱人——”全场瞬间鸦雀无声。女店员悬在空中打字的双手停止了。我不知道法官会如何处理这件事,但我很清楚,对方的失控只是将“剑柄”握在了我们手中。我没有退缩,直接指出对方公然侮辱我们的人格、散布谣言。我要求立即复印审判视频整理证据,并明确表示要报警,将案件追查到底。听到“报警”两个字,陈文汉立刻意识到不对劲。他冲过去抓住了父亲,试图向法官解释,父亲只是一时冲动。但现在他们已经失控了。我对陈文翰说:“陈文翰,你听到了吗?你的父亲在法庭上辱骂你的妻子是‘贱人’,你同意吗?你家里是靠你所谓的‘贱人的钱’养活你的吗?” “你受过高等教育,这就是你的价值吗?” “住口!”老者彻底疯了。他冲到栏杆前,挥舞着拳头,就要打我的脸:“打你怎么了?你不听话就该打你!我也打你——”看到陈爸爸又冲进来,我猛地把小雅拉到了身后。当时,我的手心已经冒出了大汗。理性告诉我,这是一个机会——只要如果他们在法官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的真实本性,则该保护令通常会有效。但情感上,看着眼前这个眼睛发红、青筋暴起的男人,我心里真想:如果这个老头真的疯了,在法庭上对我实施暴力袭击怎么办?如果法官仍然认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家庭斗殴,并给了他们每人50拳怎么办?在这样做的过程中,我押注于我们本性对暴力的厌恶。我停止了心跳,转向法官,试图保持冷静,但音量却不知不觉地变大了:“法官,你看到了他们对小雅的真实态度。他们不仅以前多次打败过小雅,而且以后肯定还会继续遭到殴打。我请求法院立即发布保护令,避免悲剧的发生。”那一刻我真的在想,如果法官还不接受的话,我还能做什么呢?为了消除法官对偏袒任何一方的担忧,我重申保护令是只是一个“保护”屏障。只要对方不实施暴力,这张纸对他们的生活就没有真正的影响;这也让他们的当事人小雅的人身安全更加有保障。这时,陈文汉意识到父亲遇到麻烦了,连忙将父亲推回了座位上。他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,转头向法官求情:“法官,误会都是误会,是他们先惹恼了我,我父亲平时很诚实,但他就是不生气……” “你诚实吗?证据会说话。”我没有给他完成伎俩的机会,直接指着法庭上的4000元收据道出了真相:那天他分明是带人闯入小雅家闹事的。警察赶到后,他在派出所躺下翻了个身,威胁说不交钱就不站起来。小雅转账只是为了“送钱给上帝”瘟疫”。“钱来了,立刻站起来。为什么,搬家也能治病?”不等他反驳,我立刻扔出他威胁小雅的证据,问道:“小雅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,想把孩子送回奶奶家,你却说‘敢送就推到河里淹死’。陈文汉,你配得上叫爸爸吗?”法庭内,又一片寂静。法官拿起我们提交的证据,盯着被告人坐的地方:“被告人,你父亲刚刚在法庭上承认,‘如果你不听话,就会挨打’。”那么,这些证据上显示的伤势都是真的,对吧?” 陈文翰愣了一下,犹豫着辩解道:“不……这不是殴打,法官,这只是……家庭纠纷,纠纷……” 法官没有听他的解释,继续问道:“那你父亲刚才说,小雅会继续被打。”如果她将来不服从的话。这是真的吗?” “不!绝对不是!那不是打……”陈文汉仍然极力否认。最后,法官说道:“好吧,鉴于你刚才的表现以及已经发生的事实,我认为这个保护令是有必要的。至少可以让大家冷静下来……” “冷静干什么?!” 法官还没说完,陈文汉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,指着法官的鼻子威胁道:“这份保护令你不能签!如果你敢发出保护令,我不会解雇你。我天天上法庭闹事!”他的父亲也站起来说道:“就是啊!我为什么要这样做?会给我儿子带来不好的名声!何况,他还应该被打!”这时,法官怒笑起来,一边飞快地整理着卷宗,一边冷冷地说道:“被告人,我到了最后一刻还在犹豫。但现在,你们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了,我必须发出这份抗议书。行动命令!休庭!”这一次,刚才还生气的父子俩终于意识到“不对劲了。”他们留在蜂巢上不肯离开,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话试图赔罪:“法官,你刚才生气了,我并没有真正伤害他……”法官头也不抬,只是摆摆手:“保护令只是一纸空文。陈文汉的家人被法警请来了。我经过的时候,听到刚刚痛哭流涕的男子低声嘀咕:“赚两块钱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”在他看来,小雅不是一个“伤害者”,而是一个“犯了错误需要纠正的人”。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在门外,法官才缓缓向我们走来:“袁律师,我今天就做出保护令的决定,明天就可以拿到了。”直到这一刻,小雅才真正明白了。恢复。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紧张的情绪彻底放松,她又放声大哭起来。法官看了看小雅,又看了看我,叹了口气。怒:“袁律师,你真是勇敢啊,今天老夫冲你冲过来的时候,你不害怕吗?” “害怕的。”我看着还在颤抖的小雅,苦笑了一下。我的腿确实软了,“但我更怕小雅会死。”小雅哭着发泄痛苦,法官补充道:“以后让你的当事人管住那张嘴吧,他骂得太过分了,如果你现在不露出他的真面目,我真怀疑他‘活该’。”从法庭出来时,阳光相当刺眼。虽然这场战斗我赢了,但我心里的阴云却没有消失。刚才陈文翰的咕哝声让我有些不安。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。按照他的逻辑,小雅不听话,想要离婚。这是挑衅。所以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实施暴力,他觉得自己是在“管理自己的行为”。就在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,路边的树后突然出现了两个黑影——陈文翰父子并没有离开。法官都下达了保护令,你还敢伤人?!我一边喊着,一边用身体护着瘦弱的小雅,往法院保卫室的方向退去。“等你来拿!”陈文翰一脸怒气冲冲地说。幸好路边有出租车站。我赶紧把小雅放进车里,小雅看到我独自面对着陈家人和她的儿子,她想下车面对他们。帮帮小雅,还是我把自己推过去边缘?如果法官今天不生气怎么办?如果保护令不起作用怎么办?但我发现我别无选择。因为每当我犹豫的时候,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小雅哭着说的“袁律师,救救我”。有些案件只有在您准备好后才会受理。你就站在那儿,别无选择。那天以后,我坚持每次开庭都要请法官让我们走十分钟,并请法警护送我们。于是,在随后的每次法庭审理中,都出现了民事诉讼中罕见的“法警值班”的情况。每次审完后,法警都会拦住他们,让我们先离开。即便如此,我们也一度在法庭外被亲属包围、辱骂……终于,来之不易的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下达了。看到这个决定,我和小雅都松了一口气。现在有了这个法盾,我终于可以挡住小雅面对的拳头了。 拿到保护令后的最初几天,夏阿弥仍不敢放松。他担心地问我:“袁律师,这篇论文真的有用吗?他真的不回来了吗?”我当时满怀信心地安慰她:“放心吧,这是朝廷的命令,他要是敢违背,后果是他承担不起的。”此后,陈文汉冷静了一会儿。他偶尔会出现在小雅的工作场所几次,但小雅报警后就逃跑了。与此同时,他也再也没有出现在小雅的住处附近。几个月过去了。小雅慢慢放下了警惕,开始相信我的话——她安全了。可谁也没想到,当我们都以为是时候翻过这一页的时候,陈文翰却回来了。四个多月后的一天,小雅突然给我发了一些照片。点开大图的那一刻,我的心猛地一跳,感到一阵寒意。那是他的体检照片,他的头皮上有一块秃了,头发被拔掉了很多,他的手臂也被拔掉了。身上布满了血淋淋的划痕。当晚,他下班后就直接叫了一辆网约车。上车前距离单位门口仅十几米。早已等候多时的陈文汉突然带着一群亲人冲了过来,将他团团围住。小雅奋力逃脱,上了车。陈文汉在车上追赶并殴打了他。路人想要打架,结果却把小雅从车里拉了出来,拖到了地上。光是看照片,我就已经感受到了痛苦和绝望。我既愤怒又内疚。令他愤怒的是,这个家庭无法无天;让她感到内疚的是,是我告诉她“有了保护令,她就会安全”。现在这些伤口,虽然我没有,但感觉就像是被人打在脸上一样。我立即收集了所有证据,再次向法院申请:陈文汉严重违反保护令,必须入狱!我本以为这笔交易很划算,结果却被法官泼了一盆冷水。拒绝拘留。很现实,法官的解释也很严厉:“袁律师,他态度不好。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,你们还在离婚诉讼中,你们还有孩子,如果他坐牢15天,第16天就出来了怎么办?如果他打碎罐子,用刀刺伤人,或者伤害别人,后果谁来承担?”我张了张嘴想要反驳,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今天回想起来,保护令制度确实具有强大的威慑力。现在的保护范围不仅限于虐待、恐吓、间谍活动,更重要的是,如果被告胆敢违反禁令,情节严重的,将被定罪入狱。但当时的规则并不像今天那么明确。法官的担忧也是现实的。这是当前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司法——我们要用法律来惩罚不法分子,但也要注意不要“让不法分子太愤怒”。听起来很荒唐,但是为了当事人的生命,我们也只能承受。最终,法院依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对这一严重暴力行为处以1000元罚款。收到决定的那天,我感觉那张纸很轻,却很沉重,令人窒息。 1000元。这就是一个女人当街剪发、尊严被践踏所付出的代价吗?与此同时,我也接到了对方律师的电话。他的语气很专业,带着审慎的鼓励:“袁律师,我们都是代理人,办案的时候,不要过多地卷入当事人的情感纠葛。”我回答:“不是,我们是在事实和证据上讨论。” “我就直说吧,”他突然语气一变,“袁律师,你的委托人太卑鄙了。”我愣了一下,没想到同事之间都会使用这样的话。他继续表达自己的偏见:“你看看审判前的他,那一刻他像泼妇一样咒骂,全程嚣张,这种人……”那一刻,我再次感受到了悲伤的“完美受害者”逻辑。在他们眼里,小雅被打、被威胁,哭不出来,闹不出来。只要她破坏、战斗,她就成了“傻子”,送妻子去医院的男人,就成了被狡猾欺负的老实人——注意说话。 “律师。我冷冷地打断她的话,“我比你更清楚我的委托人是什么样的人。按照你的说法,应该在家打她才对吧?”挂断电话后,我叹了口气,压下了心中的怒火。这次谈话我没有告诉小雅。在整个案件中,她已经受够了冷眼和偏见,我不想让她知道,即使拿到了法律文件,偏见依然如山。仍然在那里。那个时候,小雅的整个人格也随之思考,变得安静……有一天,她也安静了。我疯了吗? ” 我愣了一下,她低下头,声音很轻,“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本来就很受人尊敬。 ”她说,最近她照镜子时,看到里面那个衣衫不整、紧张的女人,她感到很震惊。“有时候我在想,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?如果不是,他为什么盯着我?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不是抱怨,而是认真思考。这就是我最不舒服的地方——她明明是受害者,却迫使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“罪有应得”。我知道单靠安慰是没有用的。如果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,我们不能等他打,我们必须主动出击。‘房子的事’,受害者没有办法回转;当法律最终介入时,恶人之前的“家事”让他得以逍遥法外,这次我不得不砍掉这个“家事”的遮羞布。当晚,我独自坐在办公室,把这几个月来的案卷、记录、证据材料全部摆在桌子上,决定从头到尾仔细过一遍,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。这次筛选,确实让我抓住了之前忽略的“致命点”。在之前的庭审中,我只认为这是“敲诈勒索的证据”,以证明该男子是无赖。我立即联系小雅,了解当天除了4000块钱,小雅在她心里只是简单地称之为“被推翻”的民事纠纷,但在我看来,这是一起被压制的“家事”。立案? ! “我几乎增长了多少世界末日。 “警察来了,但我母亲已经被救护车带走了。”小雅低着头,声音颤抖着,“陈文涵就躺在派出所里翻来覆去,说被邻居打了,不交医药费就起不来。警察见卡那副凶恶的样子,形容这是‘互相打架’,建议调解。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着我妈,只想着把她从我身边赶走,而我妈要的就是我。我就转学了。”私下4000元……”最致命的是,小雅此时并不知道这可能是刑事犯罪,并申请损害赔偿。她错过了整理证据的黄金窗口,现在才能回到冰冷的病历中。小雅还表示,后来陈文涵还打伤了她的哥哥,她的弟弟也回应称这是家里的事情。那一刻,我气得想把桌子打碎,但我又焦急万分。我们说我不能说话。通过这些细节,我再次看到了小雅的致命弱点——她并不软弱,她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邪恶。当陈文汉带着一群人去敲门时,小雅妈妈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。相反,他下意识地想要保持尊严,甚至邀请他们坐下来吃饭,试图“好好谈谈”。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善良、通情达理。从事法律工作这些年,我见过很多坏人和坏事,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为受害者感到心痛。了解了来龙去脉后,我立即指示小雅:即使当时没有身份,所有的报警记录和医院记录也必须拿到。只要打人的事实存在,只要医生记录了造成的伤害,他就不能忽视。这4000元不是赔偿,ngunit“故意伤害”铁证如山!请妈妈再次报警,详细描述事件,并坚持进行损害评估。如果创伤不可见,则可以使用当时的医疗记录和影像数据。在审查证据的过程中,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——该男子的支付宝票据是对方律师在申请保护令前两天发送的。初衷是为了管理家庭开支。在拥挤的支付流程中,我发现了两份几乎不起眼的订单——一套“叫死你”软件和一些“微键GPS定位器”。该追踪器的购买页面明确注明“用于间谍用途,待机时间太长”。那一刻,一切终于明白了。微型定位器很可能原本藏在小雅的随身物品中或者汽车的角落里。难怪小雅之前换过手机和卡,但是都不起作用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人身保护令下达后的几个月里,陈文汉只能去工作单位寻找小雅。并不是因为他突然害怕了法律,而是因为我让小雅把他的东西彻底清理干净,不小心切断了他的追踪信号。不是他不想在家里闹事,而是他找不到小雅的家。既然你习惯了躲在黑暗中射出冷箭,这次我就要把你拉到阳光下,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这又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拉锯战。尽管伤势严重、证据可信,但当时办案机构仍倾向于将其视为“斗殴事件”。我们的刑事起诉一次又一次碰壁。关键时刻,保护令成功。有了这个“官方背书”,侦查人员对案件性质的判断终于发生了改变,侦查速度也大大加快。最终,正义迟来却又到来——法院判决陈文涵有罪f“故意伤害”,判处9个月监禁;他的母亲被判处7个月监禁。这句话,让陈文翰的父亲毫发无伤。因为公安调查,他在电话里给我打电话求饶,他说只要小雅撤回指控,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,他同意立即离婚,放弃监护权,甚至不要求分割小雅婚前财产76万元。当我不肯放手的时候,他又提出了一个可笑的要求:能把所有的罪孽都交给他吗?如果不是看到这一家人的面容,我差点就会被这个“孝子”所吸引。在电话里,我严格告知他:作为一名律师,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忠实地转达给委托人,绝对不存在任何私人干涉的可能。不存在“撤销”刑事指控的说法。如果您确实想谈论调解,请带您的律师去警察局虱子站正式处理事情。若有达成协议,则要看办案机构是否同意。这绝对不是我们私下可以做的事情。陈文翰见我不帮忙,又继续说道:“袁律师,你们律师不是总是‘吃原告吃被告’吗,这样你也可以帮我,我也可以付钱给你……”我直接打断他:“既然立案了,那就交给法律吧。”吃原告,吃被告——他认为是律师最大的误会,作为与我和解的筹码。或许在他这样的人眼里,只要把钱摆上台面,就能收买所有人的良心。陈文汉见我完全拒绝,又恢复原状,在电话里咒骂我和小雅。我没理他,挂了电话。到头来,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他和他顺从的母亲。在这个宗法家庭里,父亲是皇帝,儿子是太子,母亲是皇帝。她只是一颗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。在陈文涵被立案并再次延长保护令的同时,小雅的离婚诉讼进展非常顺利,案件很快就结案了。小雅拿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和应得的财产,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 一年多后,小雅的微信再次点亮了我的手机。我以为它是在向我介绍一家企业,但当我点击它时,它又请求帮助。原来,陈文翰刑满释放。这次他学得不错,没有直接行动,而是了解到“人是恶心的”。他以“要求减少子女抚养费”为由,在数百公里外的家乡起诉了小雅,并申请冻结账户。小雅被迫离开,返回家乡应诉,但开庭当天,陈文翰并没有到场。法院驳回上诉e.但一个月后,他再次提起诉讼。这种“狼来了”的游戏他永远玩不厌。那时候,小雅最害怕的就是手机响了。当她看到法庭传票的时候,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犹豫了很久,他给我打电话,询问是否可以委托我回老家应诉。听了他的描述,我松了一口气。只要不是暴力伤害,这种无赖的伎俩在我眼里就是幼稚的。 “小雅,你没必要为了这种小事花钱请律师。”我告诉他:“但是这一次,你必须自己让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低声问道:“真的……可以吗?只有我吗?”我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教他整理好所有传票和居住证明,并写了一份《管辖权异议申请书》和一封向法院申诉的信。信中只强调了一点t:原告恶意利用庭审过程,多次提起诉讼、无故缺席,对被告进行骚扰。材料寄出没几天,小雅就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——不是管辖权异议,而是男子撤诉。他把截图发给我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:“袁律师,看来他这次不闹了。”我知道对于西奥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打赢官司。但他第一次发现,自己不需要躲在律师后面,他也可以打倒坏人。生活似乎终于回到了正轨。不幸的是,坏人不会那么轻易停止。 2023年冬天的一天,离婚六年后,陈文翰裹紧自己,走进了小雅的小区。恐惧是有记忆的。尽管他刻意遮住了脸,小雅还是从猫眼里认出了他,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陈文翰徘徊在门,用猫眼擦着脖子。警察来了,他就逃跑;警察来了,他就逃跑。当警察离开时,他会以鬼魂的形式重新出现。即便是偶尔,他也有一套说法——他来看望孩子们,不打架,不打人,不跟居民闹事。警察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阻止他们。他还开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“君子报仇不晚”之类的疯狂言论,截图很快就发给了小雅。面对这种“不违法但卑鄙”的骚扰,常规方法实在是无效。 “袁律师,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他吗?”小雅的声音里透着许久未见的无奈。 “既然他不遵守武德,那我们就用魔法来战胜魔法吧。”我让小雅把陈文涵的照片、朋友圈截图、那个人的保护令、离婚判决书、刑事定罪书都拍下来,直接放到网上经理的办公桌。 “你看清楚,这家伙有严重的暴力前科,在监狱里,现在天天在小区里闲逛哦,如果再允许他,如果有人被杀了……”小雅看着经理的眼睛,一字一顿地说,“你们物业公司是第一责任人,物业的态度并不积极,他们用一种有些责备的方式解释道:“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,大家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……”但这一次,小雅没有退缩。他自己打印了数十张告示,上面贴有陈文汉的照片和判决书截图,并称:“此人态度暴力。请业主注意安全。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,工作人员应立即报警。”他要求物业公司将这些告示张贴在门禁和电梯入口处,否则他将拒绝支付物业费并向Houseiof和Urb投诉an-农村发展局。从那天起,社区治安就加强了。陈文翰已经无法再潜入社区了。由于无法进入小区,陈文汉将目标瞄准了孩子们。孩子放学了。幸好有路人拦住了他,才没让他得逞。然后,小雅给我打电话,几乎浑身发抖。我让她带孩子去医院做心理评估,并申请暂停探视权。但在法庭上,陈文翰依然展现出了父爱。当法官问男孩是否想见父亲时,男孩只说了一句话:“爸爸太可怕了。” “那不是指责,那是一种本能。暂停访问的决定来得很快。小雅告诉我,她真的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避开坏人。一年后,2024年的某一天,我的手机再次震动,“小雅”的名字在屏幕上跳动。我的心突然一沉,一种熟悉的预感袭上心头。我……当即离开会议室,深吸一口气,吸了一口气。 “喂,袁律师……”电话那头小雅的声音有些犹豫。我握紧了电话:“别怕,她是不是又搞事情了?”不,不是!小雅说她有了新男友,想咨询再婚的法律问题。他说,这一次,他要认真地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听着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未来的打算,我突然意识到——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求助了。挂断电话后,我站在窗前,良久没有动。多年来,我陪伴他经历了报警、取证、立案、庭审、量刑、事后处理等过程。缓解骚扰,每一步的防御和攻击。每一步都不高贵,也不轻松,甚至不能称之为“胜利”。我们只是坚持住,把他从“快要被拉回来”的边缘拉了回来。但现在,他终于不用依靠这些方法来确认自己是否安全了。直到这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,有时法律是非常缓慢和有限的。它不能使一个人再次完整,不能消除恐惧,不能保证没有痛苦的生活。但经过反复使用,却可以为一个即将被吞噬的人守住底线,不至于被拖回最黑暗的深渊。而正是底线让人们有机会再活一次。每当网络上出现家暴新闻,评论区总会出现一些看似合理的问题——“为什么不报警?”“为什么不离婚?”“肯定是一个准备打架,一个准备受苦了。”“这些话看似简单,实则不多。”人们真正设身处地地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:当恐惧、怀疑和优柔寡断使一步比另一步更难自己迈出的时候。袁律师表示,这些年来,法律逐渐发展起来。财产规则更加明确,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更加明确。很多系统的发展看似前进了一小步,但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处境——比如最终被更多人认识并开始实际使用的人身安全防护令。正是在这些变化中,他逐渐意识到系统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。当它真正被激活时,可以为陷入困境的人争取一些喘息的空间,甚至一条出路。但在她遇到的客户中,亲密关系破裂时的优柔寡断、焦虑和旧病复发几乎从未消失过。他见过不断回来咨询但无法想象离开的客户;他还看到了更多看似平静但慢慢崩溃为长期消耗的关系。因此,在这个系列中,他更愿意记录的不仅仅是输赢和结果,而是这十年来人们如何逐渐理解婚姻、界限和“离开”这件事。通过关注本系列,您将看到真实的故事被看到和理解,并且选择的负担不必由所涉及的人独自承担。 (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)编辑:岳半明蒸蛋配插画:大乌花
特别声明:以上内容(如有,包括照片或视频)由自媒体平台“网易号”用户上传发布。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。
注:以上内容(包括图片和视频,如有)由网易号用户上传发布,网易号为社交媒体平台,仅提供存储服务信息。